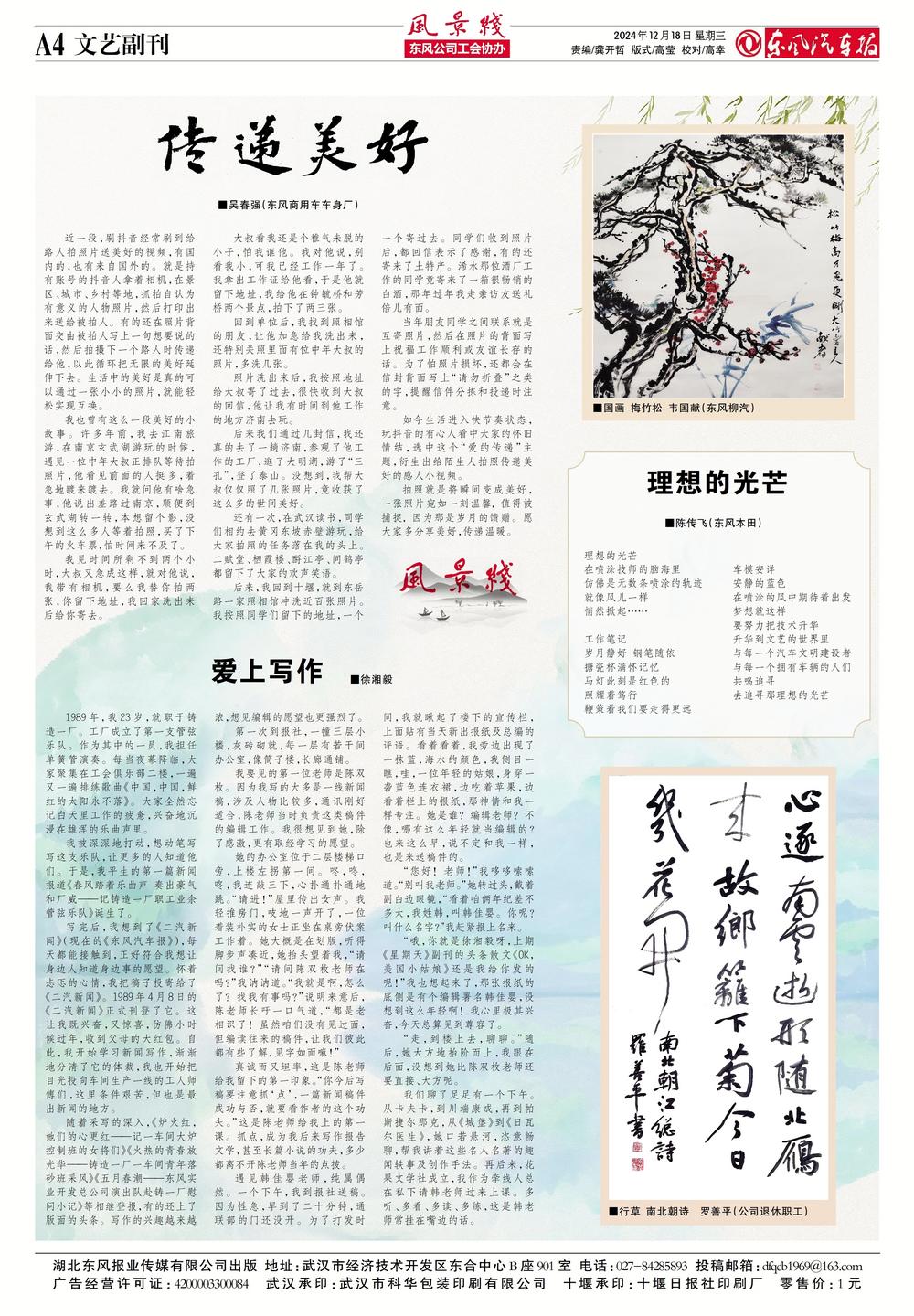■徐湘毅
1989年,我23岁,就职于铸造一厂。工厂成立了第一支管弦乐队。作为其中的一员,我担任单簧管演奏。每当夜幕降临,大家聚集在工会俱乐部二楼,一遍又一遍排练歌曲《中国,中国,鲜红的太阳永不落》。大家全然忘记白天里工作的疲惫,兴奋地沉浸在雄浑的乐曲声里。
我被深深地打动,想动笔写写这支乐队,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。于是,我平生的第一篇新闻报道《春风踏着乐曲声 奏出豪气和厂威——记铸造一厂职工业余管弦乐队》诞生了。
写完后,我想到了《二汽新闻》(现在的《东风汽车报》),每天都能接触到,正好符合我想让身边人知道身边事的愿望。怀着忐忑的心情,我把稿子投寄给了《二汽新闻》。1989年4月8日的《二汽新闻》正式刊登了它。这让我既兴奋,又惊喜,仿佛小时候过年,收到父母的大红包。自此,我开始学习新闻写作,渐渐地分清了它的体裁,我也开始把目光投向车间生产一线的工人师傅们,这里条件艰苦,但也是最出新闻的地方。
随着采写的深入,《炉火红,她们的心更红——记一车间大炉控制班的女将们》《火热的青春放光华——铸造一厂一车间青年落砂班采风》《五月春潮——东风实业开发总公司演出队赴铸一厂慰问小记》等相继登报,有的还上了版面的头条。写作的兴趣越来越浓,想见编辑的愿望也更强烈了。
第一次到报社,一幢三层小楼,灰砖砌就,每一层有若干间办公室,像筒子楼,长廊通铺。
我要见的第一位老师是陈双枚。因为我写的大多是一线新闻稿,涉及人物比较多,通讯刚好适合,陈老师当时负责这类稿件的编辑工作。我很想见到她,除了感激,更有取经学习的愿望。
她的办公室位于二层楼梯口旁,上楼左拐第一间。咚,咚,咚,我连敲三下,心扑通扑通地跳。“请进!”屋里传出女声。我轻推房门,吱地一声开了,一位着装朴实的女士正坐在桌旁伏案工作着。她大概是在划版,听得脚步声凑近,她抬头望着我,“请问找谁?”“请问陈双枚老师在吗?”我讷讷道。“我就是啊,怎么了?找我有事吗?”说明来意后,陈老师长吁一口气道,“都是老相识了!虽然咱们没有见过面,但编读往来的稿件,让我们彼此都有些了解,见字如面嘛!”
真诚而又坦率,这是陈老师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。“你今后写稿要注意抓‘点’,一篇新闻稿件成功与否,就要看作者的这个功夫。”这是陈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。抓点,成为我后来写作报告文学,甚至长篇小说的功夫,多少都离不开陈老师当年的点拨。
遇见韩佳婴老师,纯属偶然。一个下午,我到报社送稿。因为性急,早到了二十分钟,通联部的门还没开。为了打发时间,我就瞅起了楼下的宣传栏,上面贴有当天新出报纸及总编的评语。看着看着,我旁边出现了一抹蓝,海水的颜色,我侧目一瞧,哇,一位年轻的姑娘,身穿一袭蓝色连衣裙,边吃着苹果,边看着栏上的报纸,那神情和我一样专注。她是谁?编辑老师?不像,哪有这么年轻就当编辑的?也来这么早,说不定和我一样,也是来送稿件的。
“您好!老师!”我哆哆嗦嗦道。“别叫我老师。”她转过头,戴着副白边眼镜,“看着咱俩年纪差不多大,我姓韩,叫韩佳婴。你呢?叫什么名字?”我赶紧报上名来。
“哦,你就是徐湘毅呀,上期《星期天》副刊的头条散文《OK,美国小姑娘》还是我给你发的呢!”我也想起来了,那张报纸的底侧是有个编辑署名韩佳婴,没想到这么年轻啊!我心里极其兴奋,今天总算见到尊容了。
“走,到楼上去,聊聊。”随后,她大方地抬阶而上,我跟在后面,没想到她比陈双枚老师还要直接、大方呢。
我们聊了足足有一个下午。从卡夫卡,到川端康成,再到帕斯捷尔那克,从《城堡》到《日瓦尔医生》,她口若悬河,恣意畅聊,帮我讲着这些名人名著的趣闻轶事及创作手法。再后来,花果文学社成立,我作为牵线人总在私下请韩老师过来上课。多听、多看、多读、多练,这是韩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。